陳忠實(shí),1942年生于西安市灞橋區(qū),1965年初發(fā)表散文處女作,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(xié)會(huì),已出版《陳忠實(shí)小說自選集》三卷,《陳忠實(shí)文集》七卷,散文集《告別白鴿》等30余種。《信任》獲1979年全國短篇小說獎(jiǎng),《渭北高原,關(guān)于一個(gè)人的記憶》獲1990-1991全國報(bào)告文學(xué)獎(jiǎng),長篇小說《白鹿原》獲第四屆茅盾文學(xué)獎(jiǎng)(1998年),現(xiàn)任中國作家協(xié)會(huì)副主席,陜西省作家協(xié)會(huì)主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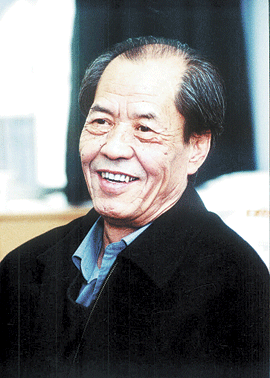
忙過“白鹿原”年
陳忠實(shí)是我認(rèn)識(shí)的最沒有架子的大作家,年過花甲的他精力充沛,厚道淳樸,只要自己能辦到的事絕不推辭,從他“溝壑縱橫”的臉上你就能感受到關(guān)中農(nóng)民特有的氣質(zhì)。“唉,我這性格這輩子都不會(huì)變了,為啥?小時(shí)候在農(nóng)村就是個(gè)乖娃嘛!”他說。
但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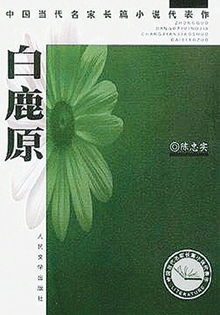 采訪陳忠實(shí)卻極難,不是他拒絕采訪,而是太忙。陜西文藝界都說今年是“白鹿原”年,電影、電視劇、歌劇、話劇齊上陣,這不但讓其他作家眼熱,連陳忠實(shí)自己都有點(diǎn)招架不住:“《白鹿原》出版也有十年了,到現(xiàn)在每年都有三四萬冊的銷量,不斷再版,讀者熱度不減,不知道是咋回事?”
采訪陳忠實(shí)卻極難,不是他拒絕采訪,而是太忙。陜西文藝界都說今年是“白鹿原”年,電影、電視劇、歌劇、話劇齊上陣,這不但讓其他作家眼熱,連陳忠實(shí)自己都有點(diǎn)招架不住:“《白鹿原》出版也有十年了,到現(xiàn)在每年都有三四萬冊的銷量,不斷再版,讀者熱度不減,不知道是咋回事?”
一個(gè)多月前我給他打電話,電話那頭陳先生的嗓門挺高:“我在原上陪北京人藝的導(dǎo)演林兆華、演員濮存昕體驗(yàn)生活呢,你來不來采訪?”我一驚,那天西安的氣溫已達(dá)到39℃,60多歲的人了,還頂著太陽走村串巷。“您可注意身體,別中暑了!”我提醒他。“沒事,走樹陰下不太熱。”真拿這老頭沒辦法。一個(gè)月轉(zhuǎn)眼過去,在我的不斷催促下,陳先生終于決定“接見”我,不過只有一個(gè)小時(shí)。
“能人”受益在《論語》
與陳忠實(shí)交談,分明能感到他深厚的“農(nóng)民”情結(jié)。他說不論自己走得多遠(yuǎn),根永遠(yuǎn)在陜西農(nóng)村。“我爺爺和父親都是有點(diǎn)文化的農(nóng)民,爺爺還當(dāng)過幾年私塾先生,家里多少有幾本書,肚里也就相對多點(diǎn)墨水。因此,在村里,我小小年紀(jì)就顯現(xiàn)出管理才能,是個(gè)‘能人’。誰家過紅白喜事,給娃慶滿月,都請我記賬,分配香煙、瓜子、糖果。有些農(nóng)民家窮,拿出的東西有限,就得巧妙地分配、掌握著使用。”
走上寫作路,是因?yàn)橐槐臼殖瓡!拔倚r(shí)候很調(diào)皮,一次爬到老家的樓上,發(fā)現(xiàn)一個(gè)破木箱,打開一看,里面放著一本用毛筆謄抄的《論語》,那字體非常工整,父親說那是我爺抄的,我壓根不信,簡直跟印刷的一模一樣,我對這部書產(chǎn)生了濃厚興趣,雖然里面的句子似懂非懂,但從中竟也悟出一些道理。那時(shí)候不懂收藏,蟲吃鼠咬,屋頂漏雨,那部《論語》最后竟不翼而飛了。”
陳忠實(shí)眼下除寫些短篇和散文,為下一部創(chuàng)作積累生活素材外,就是為他人的書寫序了。別人都以為像他這樣的大作家寫個(gè)千把字的序言易如反掌,陳忠實(shí)嘆道:“寫序其實(shí)很費(fèi)勁,這些作者都是我多年的朋友,我得研究他們的作品,思考作品中最可珍貴的東西,序言中不能全部是溢美之詞,但又得適當(dāng)鼓勵(lì),這個(gè)分寸要拿捏得合適。”
癡迷足球的“老玩童”
陳忠實(shí)身材高大,雖有些清瘦,但身板很硬朗。
有撈面吃,有足球看,有秦腔聽,就是陳忠實(shí)對生活的全部要求。幾十年來,不論多么忙,遇上電視上轉(zhuǎn)播籃球、足球、乒乓球賽都要收看,尤其對足球,從癡迷到漸成專家,時(shí)常在報(bào)上開專欄評球。有一年世界杯,為了避免家庭干擾,他索性在賓館包了一個(gè)房子美美地過了一把足球癮,被大伙稱作“老玩童”。
陳忠實(shí)還是一個(gè)家庭觀念極強(qiáng)的人,對孩子們面冷心軟,不護(hù)短。但他卻嬌慣孫子,他曾自豪地說:“哄孫子睡覺我最拿手。”而他的辦公室里最顯眼的地方就掛著他和小孫子的合影,小孫子表情頑皮,他慈祥地笑著。
饃不熟時(shí)不揭鍋
陜西文壇盡管是“群雄逐鹿”,但近些年很少有人拿出像《白鹿原》這樣厚重斑斕、在海內(nèi)外都產(chǎn)生深遠(yuǎn)影響的巨作。陳忠實(shí)說:“陜西在上世紀(jì)80年代曾出現(xiàn)一個(gè)青年作家群,例如路遙的《人生》就對中國新時(shí)期以來的文學(xué)產(chǎn)生重要影響。2000年,路遙推出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被當(dāng)代大學(xué)生評為最受歡迎的長篇小說。賈平凹驚人的創(chuàng)作數(shù)量,鄒志安、曉雷、京夫、葉廣芩各具風(fēng)采的散文、小說同樣震動(dòng)著文壇。20多年過去,有的已不在了。”陜西文壇的創(chuàng)作目前雖處于相對穩(wěn)定狀態(tài),但陳忠實(shí)更關(guān)心青年人,“這一代作家人數(shù)眾多,但在全國遠(yuǎn)沒有形成影響,這是我作為省作協(xié)主席最感迫切的事情。”
陳忠實(shí)深有感觸地說:“作家有一桶水,才能給讀者提供一碗水。要當(dāng)一個(gè)好作家,就得走進(jìn)生活,這是寫作的法典。一些新銳作家把寫作當(dāng)成游戲,一年出幾本書,而且很暢銷,這是快餐書,吃過即忘。而真正作家的書應(yīng)該經(jīng)得起人們細(xì)嚼慢咽,經(jīng)得起長時(shí)間的感受回味。”
回憶起自己12年前寫《白鹿原》的情景,一切歷歷在目:“我躲在鄉(xiāng)下一間小屋中整整四年,沒有干擾,沒有城里的是是非非,當(dāng)?shù)剞r(nóng)民都很淳樸,從不問你在寫什么,這就是一個(gè)作家最好的寫作環(huán)境了。”陳忠實(shí)笑說:“當(dāng)了作家反而徹底回到了農(nóng)村,很多人都以為我失蹤了,后來打聽到我在寫長篇,就議論猜測在寫什么。我捂得嚴(yán)嚴(yán)的不說。在我的感覺里,寫作就好比蒸饃,饃不熟時(shí)不能揭鍋,否則就漏氣了。”
陳忠實(shí)語
說文學(xué)邊緣化,我看不是壞事。在世界任何一個(gè)國家,不以經(jīng)濟(jì)為主體,讓文學(xué)成了中心,反倒是不可想象的。陶淵明能采菊東籬下,是因?yàn)樗艹燥栵垼绻B飯都吃不飽,即使給他一個(gè)桃花源,他也早跑出去要飯了。
歷史不只是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,它更深的層面是舊的心理秩序不斷被打破、新的心理秩序不斷形成的過程。這一過程中的人內(nèi)心會(huì)處在焦灼痛苦中,特別是文化人。魯迅小說《風(fēng)波》里有個(gè)細(xì)節(jié),某人進(jìn)城被剪了辮子,回去后家里陷入大的恐慌:沒有辮子怎么活啊?我非常欽佩魯迅捕捉歷史細(xì)節(jié)的能力,辛亥革命最形象化的“影響”都在這個(gè)辮子上了。
[編輯手記]:
原上飛白鹿
■周潔
今年是白鹿原年。
電影、電視劇、歌劇、話劇齊上陣,手機(jī)鈴聲片刻不停,各路人馬穿梭于前……面對如此亢奮的節(jié)奏,陳忠實(shí),這位扎根在“陜西驪山之南、白鹿原之北、溯灞水而上,距王維的輞川25公里的農(nóng)民的兒子”,有些疲憊,但百忙之中,他還是接受了本報(bào)的邀請,做客《文心》。
2003年9月20日,陳先生領(lǐng)隊(duì)中國作協(xié)三峽采風(fēng)團(tuán)一行50人來漢,我們有了第一次見面。一直以800里秦川自豪的他,用“雄奇、靈動(dòng)”來形容江城的山水、人文。更是贈(zèng)墨“一樓瞰古今”,抒發(fā)胸臆。
黃鶴樓古老,白鹿原其實(shí)也很古老。史載,周時(shí)原上因有白鹿出現(xiàn),乃祥瑞之兆,故稱白鹿原。因漢文帝修陵寢于此,改名霸陵原;再后來,大將軍狄青長年于此屯兵,又稱狄寨原。直到陳先生的小說《白鹿原》出版,白鹿原,這個(gè)被疏遠(yuǎn)了兩千多年的名字,響亮起來。
歷史留存豐厚的白鹿原,給陳先生的,倒不全是欣喜。童年記憶中,有“一顆美麗柿樹,因?yàn)榈艿苊妹玫囊馔庳餐觯鴳K遭攔腰砍伐”;青年記憶中,“在擔(dān)任公社平整土地學(xué)大寨總指揮的10個(gè)春天里,有一半日子靠救濟(jì)糧度過春荒”;中年記憶中,寫《白鹿原》之前,“每月掙六七十塊錢,上贍養(yǎng)老人,下?lián)嵊?個(gè)讀書的孩子,只要家里尚有白米白面,心中就很滿足。”這,不由讓我想起《白鹿原》里的一組句子:“大雪后接著是持續(xù)的冬旱的奇寒,凍死了白鹿原上的柿子樹,老樹新樹幾乎無一幸免。更有給皇帝進(jìn)貢久負(fù)盛名的火晶柿子,現(xiàn)在全都在一個(gè)冬天里絕殺斷種了。”用詞冷絕,痛入骨髓。寫下那樣的句子,陳先生是否是想到了自己弟弟妹妹?還有那些饑餓歲月?
據(jù)說寫《白鹿原》時(shí),為晚上能休息好,陳先生想出的法子——咕二兩酒。有一口沒一口的喝,漸漸有了酒癮,一般白酒來個(gè)二三兩才起了個(gè)頭。2年前,他來武漢的那次聚餐中,與十來人交杯碰盞,末了,還能潑墨弄詩,和記者談笑若定,此海量,非比一般。可惜沒見他喊一段鏗鏘秦腔,那該是怎樣的一種雄渾、高亢!
畢竟有十多年沒長篇問世了。陳先生說不是他不再熱愛寫作,“寫作就是世界上最令人愉悅和有幸福感的事情!就像肚子里有蛋的母雞,你就算把它放到草窠里它也能下蛋;當(dāng)然,如果這母雞肚子里根本就沒蛋,你把它放在皇帝的牙床上也沒有用。”“寫到我變成植物人,如果是那樣,只要有思維,我還會(huì)寫。”面對這樣的作家,等待一輩子,也不長!
[相關(guān)鏈接]:
陳忠實(shí):大家架子小(圖)
陳忠實(shí)和他的《白鹿原》
《白鹿原》
旅游景點(diǎn):白鹿原
歷屆茅盾文學(xué)獎(jiǎng)獲獎(jiǎng)名單(圖)
中國目前的主要文學(xué)獎(jiǎng)項(xiàng)簡介